推荐新闻

4月19日,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组织该校部分学者参加关于西南旱情的学术沙龙,与会学者针对西南大旱的成因、影响以及旱灾的应急管理方式来进行了研讨。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副教授雷一东指出,西南大旱的问题历史上就是一个常态,据1950年到1999年资料显示,这50年中就有19年大旱,即每两年多就有一次。
雷一东分析,旱灾是云南和贵州的常态,这主要与地理环境、整个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有关。因为当地气候就分雨季和旱季,雨季大概是5到10月份,降水占全年总量的90%,旱季则仅占10%。
雷一东表示:“这一次西南的干旱是很显然的大旱,其中除了自然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因素。”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戚顺荣也说:“我们还需要反思一下一些政策。比如,以前着重北方缺水、南方水多,有南水北调的工程,从现状来说可能还是这样,但是我们每做一个工程都要考虑趋势的问题,因为一个大工程的建设工期不是一年半载能完成的,等建成后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确实是要考虑的。”
戚顺荣认为,基础水利设施对跨季调水、缓解干旱有及其重要的作用,建设好了对防止污染等也有很大帮助。水利设施一旦落后,强劲的雨季洪水泛滥,不仅损害农业生产,同时也加剧了旱灾的危害。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李瑞昌也表示,很多水利设施对增加降雨是有作用的。农村有一个说法是,隔条田垄雨都不一般大。为什么呢?因为地面的河流湖泊乃至池塘水洼,都能因其水汽蒸发影响到周边雨云的形成。现在农村很多小水利设施消失了,要重新形成完善的局部地区地水循环需要很长的时间。
这次旱情之后会在环境上有些什么样的后遗症?李瑞昌认为,旱情结束以后,可能整个西南地区的河流都将面临微生物大量死亡,使河流自净能力一下子就下降的问题。即使再下雨,河流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办法恢复清澈。这对西南地区也非常大的考验。
复旦大学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中心副教授滕五晓认为,从风险管理或者从综合管理的角度来看,需要具体分析西南地区面临风险的情况及其可能的影响,并研究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
“目前的干旱,实际上从去年秋季就开始了。”滕五晓说,“去年秋季云南地区就持续干旱,当时没预计到问题的严重性,一直到2010年再去救灾,这从管理的角度是非常不妥、非常滞后的。它严重到这种程度了我们再去送水、打井,这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是撞击式管理方式,就是说危机爆发了才去应对。”
滕五晓指出,尽管从2003年我国的应急管理体系逐步完善,但责任主体仍然很不完善。2006年颁布的《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旱情信息包括干旱发生的时间、地点、程度、受害范围、影响人口,以及对工农业生产、生活、生态环境等方面造成的影响。但当旱情已发生后,这种趋势的分析有没有做、由哪个部门做,都还是很不明确的。
滕五晓表示,农民的生活用水如果早点得到重视,不会严重到后来那么艰难的地步。接下来要很好地反思或分析的问题,是怎么样提高干旱灾害预案的操作性。
李瑞昌认为,西南大旱与对西南地区水资源的利用有关。这一区域的水资源更适宜采用分散储水、统筹治理,这与西南地区生产和生活方式有关。当地属于云贵高原,山地、丘陵和梯田很常见,针对这种地形,小农耕种和散布居住是其基本生活形态,分散水源和多处储水才能更好地适应这一需求。
他解释,高原地区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导致形成围绕居住地的生态循环系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水源地的存在,这对微型水利设施提出了直接需求。因此,微型水利设施存在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西南地区农民生产生活的基础,同时也是保持微循环系统正常运行的“供应系统”。
李瑞昌认为,中国所采用的集中开发水资源的模式,事实上是以农村因小型水利设施功能退化而减量用水为代价的。农村减量用水,已成为农村耕种面积减少、耕地荒芜和土地退化的重要诱因。他说:“分散储水有利于改变水资源分布结构,使之更加有助于区域人民生产生活。从长远来看,随着生态持续好转、降水量不断回升,对已建水电站的水能开发也会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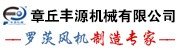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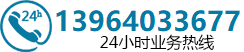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